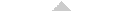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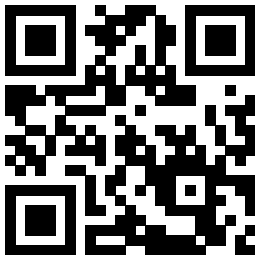

长期以来,中国产品的出口价格以低廉取胜,甚至价格之低,到了让西方国家无法忍受的程度,于是西班牙的埃尔切人放火烧了温州人的鞋,而温州人在愤愤不平之余并未认识到问题的实质,继续对自己所用的低价竞争策略津津乐道。事实上,无论是温州的打火机大王周大虎,还是鞋业大王王振韬,他们都认为价格战手段并没有错。
周大虎说,他清楚的记得打火机行业过去都是日韩企业的天下,他们的打火机价格都在200元人民币上下。温州商人们先是把价格扯下来一半,“此时日韩企业还能跟进”,但是温州人很快又把价格继续往下拉,50元、30元,“这时他们就跟不上了”。最后,一个精致的金属外壳打火机被温州商人们定位到一个日韩企业想也想不到的价格上,每只只有10元。周大虎兴奋地说,“到了这个时候,他们只有看的份了”。
温州是民营企业的天下,是按照市场经济规律运作的地方。温州的民营企业知道自己掌握有几乎在全世界最低的劳动力成本优势,把握有中国同样廉价的生产资料,所以他们可以用肆无忌惮的低价来竞争。他们所不知道的仅仅是,这一切是如何得到的,以及能否持久。而注重效率的民营企业尚且如此,范围更大的国有企业就更不必说了,即使现在是在火山之上,他们也依然会梦魇般地照样起舞。
中国经济学家们并无警觉
面对明显存在的通胀火山,太平之声,乐观之声,远不止于企业界。事实上,除了个别经济学家之外,多数经济学家对此是持不以为然的态度,而更有相当部分经济学家甚至是持完全相反的立场。比如,国内著名经济学家樊刚就一再坚持认为,中国面临的是通缩问题而不是通胀问题。他在2004年的观点依然如此,他认为:“如果今年中国的GDP增长超过10%,那么,2005年以后的中国将再度陷入深度通缩。”
而与樊刚教授持同样观点的还有很多学者,如中国宏观经济学会的王建教授同样认为未来最大的可能性是通缩。王建教授发表于2004年11月的文章认为,中国的物价上涨推动因素主要式粮价上涨和进口原油价格上涨。但从粮价看,再国内增产、进口增加和进口粮价下跌这三个因素的压抑下,粮价上涨已是强弩之末。而石油价格上涨,主要是投机因素作祟。王建引述国际能源总署数据的数据说,目前全球石油日产量为8360万桶,而需求量只有8150万桶。只是因为投机因素在导致国际油价不断攀升,而这个石油泡沫迟早会破,所以除非发生大的国际动荡,国际油价至少在明年会有显著的回落趋势。
王建认为,90年代下半期以来,中国居民收入分配差距开始显著拉开,最终需求将面临长期不足,而本轮“经济过热”主要是被投资需求拉动的,投资在当期是需求,到下一个周期就会变成供给,会使最终需求不足的情况逐步浮现出来。王建教授估计,按投资周期一般有5年时间计算,较明显的供过于求将可能出现在2008年以前,所以从目前到未来5年中,中国在物价形势方面,将极有可能从目前的“通胀”逐渐转入“通缩”。他认为,仅从短期需要出发让人民币升值,就会由于出口价格提升而丧失部分国际市场,还会因为进口增多而加重供给过剩的问题。
经济学家们往往从事的是理论研究,因此他们看问题,会沿着各自既定的逻辑路径,作出各自的价值判断。而所有这些观点、判断是否正确,最重要的是要接受现实的无情检验。问题在于,现实似乎正在大幅度地偏离多数经济学家的判断,与之背离的现实无情地摆在了我们的面前。
通胀的火山在涌动
如果说现在不断上涨的石油价格,已经掀起了国内市场价格的波浪,让我们感受到了压力和冲击,那么未来肯定还会有更多让我们吃惊的事情。近日,中国地质调查局的《危机矿山资源潜力调查与评价》对我国25种主要金属矿产10618座矿山的矿产资源形势及开发利用现状进行了分析。相关资料显示,我国现存的金属矿山大多数建于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经过几十年开采,目前已有三分之二的矿山呈现老化,保有储量严重不足,再加上近些年我国矿产勘查投入逐年减少,造成许多矿山资源枯竭、后备资源接替基地匮乏,企业生产陷入困境。
这一调查报告预期,2010年前后,将是我国大中型矿山关闭的高峰期,届时全国涉及25种主要金属矿产的大中型矿山数量,将从目前的415座急剧减少到188座。到2020年,全国有色金属矿山矿石产量每年将减少6817万吨,采矿能力每年下降8272万吨,选矿能力每年丧失7653万吨,工业产值每年减少68.38亿元,企业利润每年减少4亿多元,不但每年会减少税金5亿多元,还将有14万多人下岗或失业。
值得注意的是,这个调查报告还向市场发出了明确的警告。按照目前资源保有储量,到2010年,我国46%的主要有色金属矿山将因资源枯竭而关闭;到2020年,仅有不足20%的能维持生产。这些数据清晰地展示了一幅画面,如果在矿产勘探和替代资源方面不取得突破性的进展,中国未来矿产资源对国际市场的依赖度将会是板上钉钉的显著增加。而只要仰仗进口资源开展商业活动,维持经济运转,那就必须承担两个“后果”:一是要能与外商做价格博弈;二是要按照国际规则做生意。
目前看来,对于这两个后果国内都有严重的准备不足问题存在。在价格博弈方面,需要上有明确的战略框架,下有团结协作与游戏规则。而我们两者均不具备,反到是“三个一”非常著名,这就是“一盘散沙,一塌糊涂,一败涂地”。我们往往是作为全球最大的买家,但却毫无市场地位可言,价格总是供应方说了算,高价买进,低价卖出,无论石油、煤炭,还是钢铁,均是如此,不赔不算完。至于国际规则方面,差距就更大了,我们从温州企业做生意的方式上就可以看出,杀价竞争不但是自己人之间互相狠狠地杀,杀的性起,就是到了别人的地盘,也是照杀不误。我们的企业和商品,一方面是根本还没有打进主流市场,另一方面是对国际商业规则的一片茫茫然。我们有时会反感于态度傲慢的国外企业和外国人的所作所为,但我们没有意识到,我们在别人土地上的所作所为可能也是同样令人反感的。
也许会有人认为上述情景太悲观了,粮食今年不是增产了吗?粮食价格今年不是开始回落了吗?对此,请相信中国粮食增产是有边界的,按照经济地理学的观点,粮食增产受到土地可行性的严重制约,而我们在粮食增产上的潜力正在不断迅速流失之中。不得不提醒的是,我们在考虑中国粮食增产因素的同时,始终不能忘记的有两个问题,一个是城镇化,一个荒漠化。为了解决农民的收入问题,降低贫富差距,偿还历史包袱,我们现在“被迫”只能走城镇化的道路。而中国荒漠化之严重,荒漠化之迅速,早已世界闻名,否则各国老人退休后自愿跑到中国种树干吗?所以,只要中国的城镇化在继续,环境恶化导致的荒漠化在继续,中国的粮食问题就不可能真正得到解决。颇有意思的是,西方国家解决贫富差距是搞城市化,我们搞的却是城镇化,一字之差,却谬之千里,这意味着对环境的过渡开发,对土地大量侵占,不仅会发生在大型城市的周边,还会迅速蔓延到广大的乡村,使中国迅速地失去千顷良田,造成农地急剧萎缩,惟有大幅度提高对高价进口粮的依赖。
现实就是现实,我们不能面对现实闭起眼睛装作出不知道。就其可能性来说,我们只需想想现在石油问题的形成过程。不要忘记的是,就在三年前,也没有人肯相信石油价格将会涨到每桶50美元以上,而现在为了找到未来可用的油气资产,中国的两大石油巨头正在全球奔波,不惜冒着巨大的国际风险以高价去购买石油资产。“不可能”的事情,最终还是变成了“可能”,这在中国历史上曾经多次上演和重复。
产品价格低廉的背后
预言通货膨胀是困难的,它的困难在于这个问题为很多因素所包围,轻重缓急并不容易区分。而必须要回答一个问题是,现阶段的大量投资难道不会造成将来的产能过剩,最后导致通货紧缩吗?
客观地说,这是一种直线式的思维,表面的正确,掩盖了不正确的实质。中国之所以可以维持现在产品的低价格,原因在于四大国有银行对不良资产的粗放处置方式和源源不断地外资流入。我们可以放眼全世界去寻找,有那个国家同时存在中国这样的现象?正是这种现象的存在,使得中国企业可以使用一种非常放肆的手段进行生产,维持产品的异乎寻常的低廉价格,进行极具杀伤力的血拼式价格竞争。
具体的说,作为一家企业,它借了大量银行贷款进行固定资产投资,试图通过生产的扩大,获得一种更为经济的规模,使原有产品或是新产品具有价格上的竞争力。这种情况在经济高涨期是非常普遍的现象,问题在于,一旦这种投资失败,会出现什么样的情况呢?一种情况是企业要自己承受失败的结果,“被逼”只能通过追求更高的价格,至少也是不能随意降价,以便获取更多的利润来偿还银行的信贷;另一种情况则是无须承担投资失败的结果,因为银行可以通过“不良资产处置”,一笔勾销企业的信贷,当然这种情况下,企业也就完全轻装上阵,根本无须去提高价格,追求利润,偿还信贷了。
一个企业如此,一个项目也是如此,如果企业无须承担赢利责任,无须承担项目投资回报的责任,那么企业当然尽可以放心使用低价格的粗放方式,去生产,去销售,一切后果自有银行来承担,而银行也自有“不良资产处置办法”来解决问题。事实上,不但国有企业因此得以大胆采用低价策略,就是民营企业也间接得益,同样可以使用低价策略。其中的原因在于,民营企业所使用的信贷资金价格和生产资料价格基本与国有企业一样,只要它的初级原料和加工原料来自中国,那么民营企业就可以同样不考虑价格表现,放手利用低价竞争,不断造成产品市场价格的走低。
而中国为什么敢于使用一笔勾销式办法来处置不良资产,又与外资的持续流入有关。截至到2003年12月底,全国累计批准设立外商投资企业465277个,实际使用外资金额5041.71亿美元。这相当于4万多亿的人民币,即使去掉2万亿的不良资产,那么也还会为社会提供2万多亿的购买力,更何况外资继续在以每年400亿美元到600亿美元的规模流入中国。因此,中国产品的价格低廉,并非仅仅是因为劳动力的便宜,它的背后,还有银行不良资产处置办法和外资大量持续流入这样两个实质因素。
1999年以来,中国陆续成立了信达、东方、长城、华融四家资产管理公司,接收来自四家国有银行的不良资产,累计13939亿元,从此中国拉开了化解金融体系不良资产的“攻坚战”。2003年底,中国银行和建设银行又获得了450亿美元的外汇注资,等于又冲销了3850亿人民币的不良资产。可以相信的是,只要不良资产的处置办法继续实行,只要外资继续流入中国,那么一切问题都不会表现得太过分——即使有产能过剩,有投资失败,依然可以作为不良资产一笔勾销;即使价格有波动,也不会令人太担心,最多也只是表现为“温和的通胀”。只要这样的格局不破,那么这种明显“不太自然的”经济运行还是可以继续下去的。
对于价格火山,我们必须能够透过表面看到本质!火山之上,即使草木葱葱,也依然是火山,地下依然涌动着灼热的岩浆。我们有关通胀问题的任何推理,都不能忘记产能过剩终究是相对的,资源约束和投资效率低下则是绝对的。产能过剩,尚可以通过增加当期投资来激发消费,遇到景气周期,企业依然可以恢复弹性,甚至可能会像2003年的汽车工业那样,喊出“当初要是多投资、多增加些产能就好了”。但资源约束和效率低下就不同了,效率的提高绝非是一朝一夕的事情,有时它甚至需要几代人的不懈努力。资源约束更是因自然条件的而成为天然的问题,有就是有,没有就是没有,即使处于景气周期,资源的价格也只会更高。很显然,价格火山并非不存在,它只是为中国特殊发展时段内的云雾所遮盖。
价格火山将来会爆发吗?
中国的价格火山会喷发吗?答案是肯定的。因为目前银行对于不良资产的处置方式是不可能持续的,而外资流入的不确定性就更高了。
对于银行不良资产,穆迪在1999年和摩根大通这样的投资机构均有研究,他们认为,中国国有银行系统的重组成本可能高达GDP的18%,而根据公开披露的信息,目前国有银行的“四大”不仅与2000年世界前20家大银行3.27%的平均不良贷款率相去甚远,而且也远远高于亚洲危机前东南亚各银行6%的水平。更为严重的是,现在对不良资产的处置还有了明显的扩大化趋势,而“一笔勾销”正在日益演变成为一种令人无法理解的金融时尚。
保险公司过去有利差损和经营损失的,怎么办?注资、勾销!而这估计是一笔约近千亿规模的资金。证券公司圈钱造成的损失怎么办?同样是注资、勾销!2004年129家券商生存状态恶化,不良资产超过51%。南方证券、闽发证券等券商面临危机,并已经得到央行的救援,风险向央行作了转移。市场估计,要真正解决券商危机需要花费1000亿到1600亿人民币,而今年市场中已经传出消息说,中国政府将向证券公司提供600亿左右的“资金援助”。当然,“不良资产蛋糕”中最大的一块还是银行,因为银行业在近来连续几年的投资热中,又新产生了相当规模的不良资产(所谓不良资产指标的“双降”,除了个别经济学家之外,现实中实际上根本没人信),这样发展下去,何处是个头?这等规模的资金损失,如何能够持续下去?!显然,一笔勾销与无偿注资式的不良资产处置方式必然会有终止的一天,这样的一天,也许就会在未来3到5年里出现。
至于外资流入的不确定性就更高了,它不但关系到人民币汇率问题,还关系到货币的自由兑换,关系到投资回报和市场开放,关系到国内和国外的政情演变。事实上,世界上根本不存在“永远的资金流入”,日本如此,拉美如此,实际上美国也是如此。而外来资金嘎然而止的一天如果真的到来,已经适应了大手大脚花钱的中国,是否能够适应每年间猛然减少的四、伍千亿人民币,实在是让人感到不寒而栗,没有把握。
一句话,价格的火山是否爆发,皆系于不良资产和外资的流入,两者出问题的时候,就是价格火山爆发的时刻。

